梅雨初至,老墙上的苔藓又绿了一层。我站在外婆的灶台前,看她往药罐里添最后一把艾草,蒸汽氤氲中,她的身影如一幅被时间浸染的水墨画。“苔藓又长了,”她喃喃道,“这墙啊,快扛不住喽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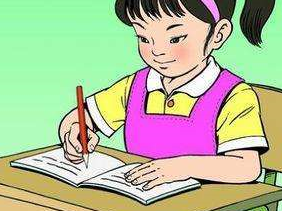
邻居们早已搬进新城的高楼,唯有外婆守着这座百年老屋。墙面斑驳,苔藓在砖缝间蜿蜒如墨迹,雨水浸润处更是翠得惊心。我总想帮她清理,她却摆手:“苔藓是墙的年纪,擦不得。”
那个夏天,台风来得猝不及防。深夜,老屋在风雨中颤抖,墙皮簌簌落下。突然一声闷响——东墙塌了一角。雨水裹着碎砖和苔藓涌进屋里,外婆却不急着排水,而是蹲下身,小心拾起那些沾满泥浆的苔藓块,轻轻放在干燥处。
天刚亮,她便召集留守的几位老人。“墙要修,”她说,“用老法子。”我这才明白,所谓老法子,竟是“以苔养墙”。老人们挖来糯米浆、石灰和黄土,按古法调制灰浆,再将收集的苔藓捣碎掺入。外婆将混合物仔细填进砖缝,动作轻柔如抚婴。
“苔藓能护墙,”她见我疑惑,轻声解释,“它的根网能牢牢抓住砖石,下雨时吸水,天晴时保湿。这老墙啊,离了苔藓才真的活不成。”
那个雨季,我每天观察修复的墙面。最初毫无动静,直到某天清晨,一抹极淡的绿意从灰浆中探出——苔藓复活了。它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,渐渐覆盖了新修的墙面,与老墙的苔藓连成一片,再也分不出彼此。
老屋终于保住了。新城来的工程师啧啧称奇,说这是“自然的智慧”。外婆只是笑笑,继续照料她的苔藓墙。
离乡前夜,外婆带我触摸墙面。苔藓柔软而湿润,仿佛大地的呼吸。“你看,”她说,“人都说苔藓是岁月的疤,我倒觉得它们是时间的针脚。一针一线,把破碎的缝补成更坚韧的模样。”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我与外婆、与这座老城,何尝不是与苔藓一起走过时间?我们都是世间的苔藓——卑微却顽强,在遗忘的角落执拗地绿着,用最柔软的根系守护最坚硬的记忆。
如今老屋已成保护建筑,墙上的苔藓翠绿如初。每次回乡,我都会俯身触摸那片湿润的绿意,仿佛触摸到时间的脉搏。与苔藓一起走过的日子里,我学会了在断裂处生长,在雨水中丰盈,并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,活成最坚韧的风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