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南的梅雨,黏稠得化不开。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老宅的天井里,青苔正沿着墙根无声地蔓延,像时光留下的绿锈。堂屋的八仙桌旁,姑婆静静地坐着,手里是一只即将成形的竹编小篮,青黄色的篾丝在她指间跳跃,发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,宛若蚕食桑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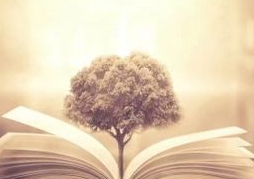
我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长大的,习惯了世界的喧嚣与更迭。在我看来,这门手艺慢得让人心焦,且毫无用处。我劝她:“姑婆,别编了,现在谁还要这个呀?”她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里漾开一丝笑意,轻声说:“囡囡,有些东西,不是做给外人看的。”她摊开掌心,那里躺着一枚温润的竹编小蝉,翅膀的纹路清晰可见。“这是留给自己的一片‘芳心’。”
“芳心”?这个词像一颗石子,投入我沉寂的心湖。我原以为它只关乎风月,此刻却觉得,它更关乎一种清醒的坚守,一种不为外界风雨所动的内在定力。我环顾这间老宅:榫卯松动的太师椅,釉色剥落的盖碗,甚至天井里那口长满浮萍的古井,它们都静默着,仿佛都在以自己的方式,为这个喧嚣的世界“留一片芳心”。
我的目光重新落回姑婆的手上。那双手,枯瘦,布满深褐色的斑点,却异常稳定。篾丝在她手中,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最后的韧性。我突然懂了,她编织的不是一件器物,而是一段可以触摸的光阴,一份对抗遗忘的温柔力量。这力量如此微弱,却如此固执,像墙角的青苔,只要有一寸土、一丝潮气,便要执拗地绿给天地看。
那个午后,我没有再说话。我只是坐在姑婆身边,听着雨声和篾丝的摩擦声交织在一起。我不再觉得这声音单调,反而听出了一种繁华落尽后的从容。
离开时,姑婆将那只小蝉放在我的掌心。它很轻,却又很重。我知道,我带走的不仅是一件手工艺品,更是一颗被古老“芳心”浸润过的种子。从此,任凭外界车马喧嚣,我的生命里,也当为这样一种无用的、审美的、从容不迫的坚守,留一片清净的芳心。它让我在奔流不息的时代洪流中,得以找到一块立足的礁石,不至于迷失方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