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五岁那年,我家从城北搬到城南。旧楼电梯里的“再见”还没褪色,新家隔壁的电钻声就撕碎了所有熟悉感。父母忙于生计,我在陌生的房间里,像一只误入玻璃瓶的飞虫,四处碰壁。成绩一落千丈,友情戛然而止,整个世界都在高速运转,只有我被遗落在某个时间的缝隙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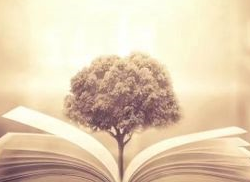
直到那个雨天,我躲进社区图书馆避雨。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与油墨混合的沉香,一排排书架如沉默的士兵列队。无意间抽出一本《瓦尔登湖》,扉页上有人用铅笔轻轻写道:“1987年春,于此自救。”字迹娟秀,仿佛某个时空的求救信号。我怔住了——原来不止我一个人,需要在这里寻找救赎。
那个下午,我在靠窗的位置读完半本梭罗。当他写下“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,吮尽生活的骨髓”,我忽然听见内心冰层碎裂的声音。原来早在一个世纪前,就有人如此孤独又如此热烈地活着。合上书时,雨停了,夕阳穿过百叶窗,在地板上烙下金色的条纹。
从此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。我在海明威的硬汉身上学会坚韧,在史铁生的地坛里读懂残缺之美,在《百年孤独》的魔幻中照见现实的荒诞。每一本书都是一扇任意门,让我暂时逃离逼仄的现实;每一行字都是一根绳索,将我从自我怀疑的泥潭中打捞起来。
最难忘的是读《活着》,福贵经历无数苦难后说:“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,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。”那一刻,我趴在泛黄的书页上,泪水模糊了铅字。所有的委屈与迷茫,终于找到安放的角落。
我开始尝试写作,把无人可诉的心事铺展成文字。起初只是笨拙的模仿,渐渐有了自己的节奏。当第一篇短文发表在校刊上时,我拿着那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,在图书馆同样的位置坐了很久。
如今我已走出那段幽暗岁月,但依然习惯在困惑时走向书架。我终于明白,能拯救自己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答案,而是在阅读中建立的、与广阔世界的连接。每一本书都是一块浮木,当无数浮木相连,便成了渡你过河的桥。
那个在图书馆避雨的少年或许不会想到,多年后的今天,他依然在用书籍搭建桥梁——不仅渡自己,也渴望渡他人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跌入自己的深渊,而书本,永远是成本最低的绳索。当你抓住它,就会发现:下坠的过程,原来也可以是飞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