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下午,阳光把尘埃照得无所遁形。母亲将一个蒙尘的铁盒推到我面前:“清清吧,没用的就扔了。”我打开盒盖,一股旧纸张特有的、混合着时光与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整理,却不知自己打开的,是一部用零碎物件写就的家族史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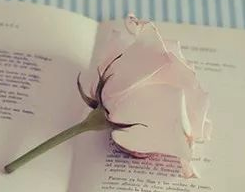
首先触手的,是一张脆硬的纸片。是祖父的“职工夜校扫盲班毕业证”,日期是1952年。纸张泛黄,印章模糊,可上面用铅笔写下的“优等”二字,却倔强地清晰。我抚摸着那笨拙却坚定的笔画,仿佛能看见年轻的祖父,在一天的劳作后,就着昏黄的煤油灯,如何用布满厚茧的手,艰难地握住笔,一笔一划地描摹着对“文化”最初的想象。这张纸,清点出的是一个家族从蒙昧迈向启蒙的起点,沉重而滚烫。
接着,是一封未寄出的信,来自1993年。那是父亲的字迹,潦草而激动,写给一位南下的朋友,信里反复计算着去广东打工可能挣到的钱数,以及对“闯一闯”的无限渴望。信的末尾被撕去一角,最终也没有封入信封。我忽然明白,这封未寄出的信,清点的是父亲人生十字路口的全部彷徨与最终留下的抉择。那一代人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、机遇与牺牲,都凝固在这张沉默的纸页里。
最后,是我自己的一叠奖状,从小学的“跳绳比赛第三名”到初中“优秀班干部”。它们色彩鲜艳,却轻飘飘的,像一层层华丽却单薄的标签。在祖父的“毕业证”和父亲的“信”面前,我那些被精心收藏的“荣耀”,忽然失却了分量。我的清点,似乎只关乎个人的、浅表的成败,而前辈们的清点,却与一个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。
我轻轻将所有的物件放回铁盒,盖好。我清点出的,哪里是“无用之物”?那分明是祖父留下的、对知识近乎虔诚的渴望,是父亲咽下的、那份沉甸甸的担当。这次清点,像一次无声的交接。我终于懂得,生活真正的价值,不在于清点自己获得了多少光鲜的凭证,而在于清点自己继承了什么,又将传递下去什么。
那铁盒的分量,此刻重若千钧。它清点出的,是我生命的来处,与我将要奔赴的远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