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日历撕到最后一页,我才发现,那些被我随手团皱的纸团,像一个个未拆的礼物,堆在桌角。窗外,冬日的太阳像一枚剥了壳的煮鸡蛋,柔软却滚烫。我伸手接住光线,掌心忽然长出一条透明的路——它穿过寒假、高考、大学,一路蜿蜒到更远的云层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认真地相信:未来可期,并非作文纸上的套话,而是正在发生的下一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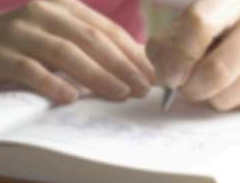
高一时,我成绩平平,像跑道里最沉默的那粒灰。一次班会,老师让我们写“给三年后的自己”。同学们奋笔疾书,我却盯着空白信纸发呆,直到笔尖无意识晕开一团墨。我画了一棵小树,旁边写:愿你长成能给别人乘凉的地方。写完后,我把信塞进信封,投入“时光信箱”,心里却想:树会不会还没发芽就被砍掉?
高二分科,我选最不擅长的理科,只为靠近“好就业”的未来。第一次月考,物理三十九分,像一记闷棍把我打进自我怀疑的沼泽。夜里,我躲进实验楼后的小竹林,借着路灯翻那本厚厚的《力学》。风把书页吹得哗啦响,也吹得我眼眶发热。我抬头,看见枝丫间挂着一枚弯弯的月亮,像未闭合的括号,等待被填满。忽然心里一动:如果月亮每晚都来,我凭什么不能重来?于是我把错题一条条剪下,贴满半面墙,每天对它们说:“明天见。”期末,物理卷上写着鲜红的“八十五”。我把试卷举到月光下,像举着一面迟到的旗帜,那棵“小树”似乎悄悄抖了一下枝条。
如今,我站在高考倒计时牌前,数字只剩薄薄几页。我不再计算与终点线的距离,而是丈量自己比昨天又多迈了几厘米。清晨六点的教室,灯光像一条安静的河,我涉水而过,把单词、公式与诗一点点装进背包。它们重量很轻,却能把前方的雾拨开一道缝,让隐藏的未来露出微光。偶尔疲惫,我就去走廊尽头,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,望见对面的工地:塔吊旋转,钢筋向上生长,一座新的图书馆正拔地而起。那一排排裸露的骨架,像巨大的树,还在等待混凝土的“年轮”。我想,它们也是我的同伴——都在黑夜里悄悄拔节,等待清晨的人来验收。
放学路上,我经过一家花店,老板娘把即将枯萎的向日葵插在门口,挂块纸板:免费送给努力的人。我挑走一株,花盘低垂,像害羞的舵。回家后,把它插在灌满清水的瓶里。第二天清晨,它竟微微抬起头,追随窗缝透进的微光。我蹲在它面前,听见心底“咔哒”一声——那是种子裂开的声音,也是括号合拢的声音。
我把那株向日葵命名为“可期”。它教会我:未来不是某个遥远的彼岸,而是此刻正在呼吸的每分每秒;是凌晨的灯光、月下的错题、工地上的塔吊,也是一朵垂头的花重新昂起的瞬间。只要我们愿意把今天过得饱满,明天就会像熟透的向日葵盘,一粒一粒,交出饱满的种子。
于是,我继续伏案,把每一次笔尖与纸面的摩擦,都当作替未来铺路。我相信,当六月的风吹过考场,我会带着满身的墨香与花香,走出那道门。而门外的阳光,一定会像今天这样,柔软却滚烫,替我揭晓最后的谜底:未来可期,其实早已在每一次不放弃的此刻里,悄悄兑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