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的院子里有一架老旧的秋千,铁链锈迹斑斑,坐板被岁月磨得发亮。小时候,我踮起脚尖,也触不到横杆,只能仰望。外婆笑着把我抱上去,轻轻一推,我便飞了起来。风从腋下穿过,像给心脏插上了羽毛。我尖叫:“再高点!”那一刻,我第一次明白,原来人也可以离天空更近——只要有人愿意推你一把,也敢把脚抬离地面。那便是我梦想的雏形:一双看不见的翅膀,藏在胸腔里,等待起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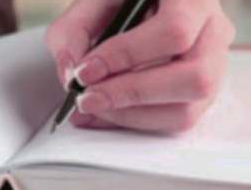
后来,我长大,秋千拆了,取而代之的是课桌、试卷与排名。我把翅膀折进书本,像折一张不合尺寸的地图书页。夜深人静,台灯把影子压成薄片,我写着“未来”两个字,却觉得它离我很远。直到高一那年,学校请来一位盲人摄影师。他站在讲台上,用耳朵对焦,用心测光,拍出的照片却通透得令人屏息。有人问他:“看不见,为什么还要拍照?”他笑:“正因为看不见,我才想让世界看见我。”话音落下,我听见“啪”的一声——那是心里的纸页被重新翻开,翅膀在血液里舒展。
我开始给校刊写稿,把文字当作底片,去冲洗那些藏在日常褶皱里的光。起初,投出的文章像石沉大海,邮箱寂静得像冬夜的湖面。我也气馁,却在此时翻出外婆的旧秋千,铁链虽锈,却仍能晃动。我坐上去,脚尖一点,吱呀声里,童年的风又回来了。它告诉我:飞,不是为了抵达云端,而是为了在跌落时,仍能听见风的声音。于是,我继续写,把被拒绝的邮件存进文件夹,取名“羽毛收集”。当第一百零三封退稿信到来时,第一篇短文终于发表。油墨香飘散的瞬间,我摸到腋下新生的风——它不大,却足以托离地面几厘米。
今年春天,我报名去山区支教。山路十八弯,大巴车喘得像老牛。夜里,孩子们在操场上围成一圈,让我讲故事。我拿出那张刊有自己文章的校刊,念给他们听。火光映着他们的眼,像撒了一把碎星。最小的女孩拉我衣角:“老师,我也想飞。”我把杂志递给她:“那就先让字带你飞。”她小心翼翼接过,像捧住一只刚出壳的鸟。那一刻,我听见自己的翅膀拍击空气——原来,它早已在一次次书写、一场场朗读里,长成能够承载他人的尺寸。
回城的车窗倒映出我的脸,也倒映出那片被月光洗净的山谷。我恍然:梦想不是终点,而是一双永续生长的翅膀。你每一次相信,它就添一根飞羽;你每一次分享,它就增一抹亮色。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太阳,但可以在奔赴的过程中,把阴影留在身后,把光投向更远的地方。
夜深,我合上电脑,耳边仿佛又响起秋千的吱呀。那声音穿越十年光阴,与山风、与火堆、与键盘的敲击声重叠,汇成同一句话:别怕飞不高,先让心长出羽毛;别怕风停,先把自己变成风。梦想是心灵的翅膀,而每一次振动,都从你愿意离开地面的那一秒开始。明天,我仍将坐在桌前,继续写字,继续收集拒绝,也收集星光。因为我知道,只要翅膀仍在生长,脚下的大地就永远无法囚禁我——天空会在每一个抬头的瞬间,为我敞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