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错别字的作文
放学时,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手里捏着我那篇《难忘的一天》。
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切进来,在作文本上投下明明暗暗的格子,那个刺眼的“级”字就趴在第三行,像只没站稳的小蚂蚱。 “你看这里,”老师的指尖轻轻点在错字上,声音比窗外的蝉鸣温和些,“‘好看极了’的‘极’,是表示程度的‘极’,像‘开心极了’‘棒极了’,都要用这个带‘木’的字。你写成‘年级’的‘级’,是不是觉得读音一样就随便写了?” 我盯着那两个长得有点像的字,脸慢慢发烫。确实是写的时候太急,脑子里想着公园里的花有多艳,手指就跟着嘴型跑了。 “作文里的字就像积木,”老师翻到我写划船的段落,“你把‘平稳前行’写得这么清楚,读者就像坐在你旁边的船上。可要是积木搭错了,船就会晃。一个错别字,可能就让读者分心了呀。” 她从笔筒里抽出红笔,在错字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:“这次改过来就好,下次写完多念两遍,像检查划船的方向一样,慢慢就稳了。” 走出办公室时,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
我攥着作文本,那个被圈出来的“级”字像颗小石子硌在心里——原来写字和划船一样,急不得,得一笔一划踩稳了,才能让别人看清你眼里的风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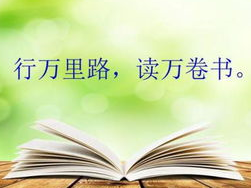
《那次写错别字的教训》
期中考试前夜,我房间的台灯一直亮到十一点。书桌上摊开的语文课本和密密麻麻的笔记,都在提醒我明天的考试有多重要。"小华,该睡觉了。"妈妈第三次敲响房门时,我的眼皮已经像灌了铅似的沉重。
第二天考场上,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试卷上,晃得我眼睛发酸。写作文时,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,笔尖在纸上飞快地滑动。"我的妈妈总是克克业业地工作......"我完全没注意到,自己把"兢兢业业"写成了"克克业业"。结尾时我又写道:"我要再接再励,争取更大进步",根本没发现"厉"字被我写成了"鼓励"的"励"。
最糟糕的是那天的重头戏——作文《我的妈妈》。我写道:"看到我生病,妈妈的轻轻'的'哭了,她'的'手温柔'的'摸着我的额头。"三个"的"字像三根刺,后来全都扎在了我的成绩单上。
发试卷那天,王老师特意把我的作文当范例朗读。当她念到"妈妈'的'哭了"时,全班突然爆发出哄堂大笑。我的脸"唰"地红到了耳根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原来那8分全扣在了错别字上,我的90分就这样变成了82分。
放学路上,梧桐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。我踢着石子,想起妈妈常说"字如其人"的话。书包里那张布满红色圈点的试卷沉甸甸的,每个红圈都像在嘲笑我的粗心。那天晚上,我特意找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把写错的字工工整整抄了二十遍。月光照在新买的错字本上,我暗下决心: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。
现在每当我提笔写字,眼前就会浮现出试卷上那些刺眼的红圈。它们时刻提醒我:汉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,一笔一画都马虎不得。那次写错别字的教训,就像刻在树皮上的字,随着时间流逝反而愈发清晰。
写错别字的“成长礼”
语文课上,我正奋笔疾书地写作文,突然,一个熟悉的字卡住了我——“尴尬”的“尬”。我盯着那个字,笔尖在纸上悬着,脑海里一片空白。我绞尽脑汁,却怎么也想不起它的正确写法,只能凭着感觉写了个“格”。
下课后,我拿着作文本忐忑地走向老师。老师接过本子,目光落在那个错别字上,轻轻叹了口气,却没有批评我,而是温和地说:“你知道‘尴尬’的‘尬’为什么是‘尢’字底吗?”我摇了摇头,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
老师接着说:“‘尢’字底在古代是一种表示角落、隐蔽处的象形字。‘尬’字的意思是躲在角落里,感到不自在。所以,它和‘格’字是完全不同的。”我恍然大悟,原来一个小小的错别字背后,竟然藏着这么有趣的道理。
从那以后,我开始留意每一个字的笔画和结构,不再把它们当作简单的符号,而是当作一个个有故事、有生命的伙伴。每当我写错一个字,我都会停下来,仔细琢磨它的来龙去脉,就像在和一位老朋友重新认识。
慢慢地,我发现错别字不再是让我头疼的“拦路虎”,而是我成长路上的“小老师”。它们提醒我,学习是一个不断探索、不断修正的过程。每一个写错的字,都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,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,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现在,当我再次拿起笔,面对那些曾经让我犯难的字时,我会微笑着想起老师的话,想起那个让我成长的错别字。
那张写满"小插曲"的作文本
整理书桌时,一本边角微卷的作文本从旧课本里滑了出来。深蓝色的封皮上还留着去年冬天的水渍,翻开第一页,"我的妈妈"四个大字端端正正写着,可再往下看,那些被红笔圈出的错别字就像一群调皮的小麻雀,在纸页间扑棱着翅膀——"已经"写成了"以经","戴红领巾"写成了"带红领巾",最让我脸红的是"妈妈的爱像温暖的阳光"里,"温暖"的"暖"右半边竟少了一横。
那是五年级上学期的一次周记作业。那天放学后,我急匆匆扒拉了两口饭就趴在书桌前写作文。妈妈端着热牛奶进来时,我正咬着笔杆琢磨开头:"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"她笑着摸了摸我的头,转身去厨房洗碗,围裙带子松松垮垮挂在身后,像条摇摇晃晃的小尾巴。
"今天数学小测我考了九十八分!"我得意地喊,笔尖在纸上沙沙走着,"妈妈接过卷子,眼睛弯成了月牙,伸手摸了摸我的头,说'以经很棒了'。"写着写着,我突然卡壳了——想写妈妈每天早晨帮我整理红领巾,却怎么也想不起"戴"字怎么写,盯着天花板发了半分钟呆,最后自作聪明地写了"带"。"她总是仔细地为我带好红领巾,说这是少先队员的标志。"写完这句我还偷偷瞥了眼作文本,心想:反正意思差不多嘛。
最离谱的是结尾。我想形容妈妈的爱像阳光,可"暖"字写到一半突然忘了笔画,急着往下赶,就少写了一横。"妈妈的爱像温暧的阳光,照得我心里软软的。"落笔时,我甚至想象着老师会在这句话下面画波浪线——毕竟"软软的"多生动啊!
第二天交作业时,我还特意把作文本摆在最上面。周三大扫除,我帮语文课代表搬作业本,瞥见自己的本子正躺在讲台上,红笔批注像小红旗一样插在字里行间。"错别字较多,需加强基础练习。"老师的评语写在文末,旁边用红圈圈出的错字旁,工工整整地写着正确答案:"以经→已经""带→戴""温暧→温暖"。
放学后,我磨蹭着不敢回家。妈妈来接我时,我低着头把本子递过去:"老师说...说我错别字太多了。"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红圈,没有像往常一样摸我的头,却突然笑了:"你写'妈妈伸手摸了摸我的头'那句,虽然'以经'写错了,但我真的记得那天你考了九十八分,我确实蹲下来跟你平视,说了这句话。"她翻到写红领巾的那页,"还有这里,'带红领巾'虽然错了,但我每天帮你整理领巾时,确实会特意把绳子抚平——你看,错别字没挡住我想表达的爱。"
那天晚上,妈妈陪我重新抄写了那篇作文。台灯暖黄的光里,她握着我的手纠正每个错字的笔画:"'暖'的右边是'爰',不是'爱',多一横就像多一层温暖;'戴'是'十'字头,像把东西稳稳托在头顶。"我忽然发现,那些被我忽略的错别字,原来都是我对生活观察不够仔细的印记——我急着表达"妈妈很好",却没注意到她系围裙时总把带子掖进衣角,没发现她给我戴红领巾时总要先哈口气把褶皱抚平。
现在再看这本作文本,那些红圈圈里的错别字早已成了特别的标记。它们提醒我:文字是有温度的,每一个笔画都承载着想传递的心意;它们也教会我,认真对待每一个字,就是认真对待生活里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珍贵的瞬间。
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作文本上,那些曾经让我羞红的错别字,此刻看起来竟像一颗颗小小的星星——它们曾经闪烁得有些歪扭,却始终亮在我成长的夜空里,提醒我:写对每一个字,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尊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