缝纫机上的月光
母亲的缝纫机总在深夜响起,咔嗒咔嗒的声响像座老钟在走。那年冬天我要参加市里的朗诵比赛,她翻出藏在箱底的蓝布,说要给我做件新衬衫。
她白天在菜市场摆摊卖菜,冻得手指关节发红。晚上回到家,就着 15 瓦的灯泡踩缝纫机,踏板压在地板上,发出规律的吱呀声。有次我半夜醒来,看见她正对着月光穿针线,线头在布面上打了个又一个结。“这布硬,得多缝几道才结实,” 她揉着发酸的肩膀笑,镜片上落着层细密的雾。
比赛前一天,衬衫终于做好了。领口处缝着圈细细的白边,针脚密得像撒了排小米粒。我穿上身时,发现袖口比平时的衣服短了半寸 —— 她总把我的尺码记错,就像总把糖当成盐撒进菜里。
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,聚光灯照得我睁不开眼。低头看见衬衫第二颗纽扣松了线,线头垂在胸前轻轻晃。忽然想起母亲缝纽扣时的样子,她把线头在舌尖抿湿了再打结,说这样才不会散。台下的掌声潮水般涌来,我却只想快点回家,看看她指尖被针扎出的小红点好了没有。
如今那台缝纫机还在阳台角落,落满了灰尘。但每当阴雨天,我总觉得能听见咔嗒咔嗒的声响,像月光落在布面上,轻轻巧巧地,就缝补好了岁月里所有的褶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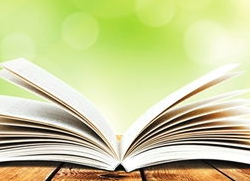
藏在毛衣针里的爱
冬天的风像小刀子似的刮着脸,我缩着脖子往家跑,远远就看见阳台上的剪影——母亲又在织毛衣了。她织毛衣时总爱把绒线绕在小指上,针尖在灯光下闪着银光,一挑一勾间,仿佛在编织整个冬天的温暖。
上周我赌气把新买的毛衣扔在地上:"现在谁还穿手工毛衣!"母亲没说话,只是弯腰捡起来轻轻拍打。夜里起床喝水时,发现她房间还亮着灯。门缝里,她正拆着那件被我嫌弃的毛衣,把旧毛线一圈圈绕成团。织针碰撞的声音很轻,却一下下敲在我心上。
今天放学时突然下雨,我没带伞,正犹豫要不要冲进雨里,却看见母亲举着伞站在校门口。她怀里揣着刚织好的新毛衣,自己半边身子都淋湿了。那件鹅黄色的毛衣带着樟脑丸的味道,领口还绣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。"绣得不好看。"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拽了拽线头,可那朵花分明在雨水中开得格外鲜艳。
晚上我穿着新毛衣写作业,绒毛蹭得下巴痒痒的。母亲在旁边织着另一只袖子,线团咕噜噜滚到地上。我捡起来时,发现她手指上全是细小的针眼,有个伤口还贴着创可贴。原来每件毛衣里都藏着这样的秘密:那些我看不见的刺伤,最终都化成了我身上的温暖。
此刻台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,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挨得很近。母亲织完最后一针,习惯性地把毛衣贴在自己脸上试了试柔软度。这个动作让我突然鼻子发酸——她总是这样,先把所有的刺都留给自己,再把全部的柔软都给了我。
《母爱如粥》
清晨五点半,厨房的灯准时亮了。
我在睡梦中听见锅碗轻轻碰撞的声音,像一首温柔的摇篮曲。母亲总是这样,在我醒来前就把一切准备好。厨房的门没关严,一缕白雾般的蒸汽飘出来,带着淡淡的米香,悄悄钻进我的房间。
我揉着眼睛走到厨房门口,看见母亲正俯身在灶台前。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袖子挽到小臂,手腕上的银镯子在晨光里闪了一下。砂锅里的小米粥正"咕嘟咕嘟"冒着泡,她拿着木勺小心地搅动,手腕转得很轻,仿佛怕惊扰了什么。
"醒了?"母亲回头看见我,眼角立刻堆起细碎的笑纹,"再躺会儿,粥快好了。"她的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,手指却灵活地往粥里撒了一小把枸杞,红艳艳的籽粒像落在水面的花瓣。
我靠着门框看她盛粥。白瓷碗边沿凝着细密的水珠,在晨光里微微发亮。母亲吹了吹热气,舀起一勺吹凉,递到我嘴边:"尝尝烫不烫。"我低头喝下去,米粥绵软温热,枸杞的甜味在舌尖化开,连呼吸都染上了粥香。
忽然发现,母亲的手指比去年更粗糙了。昨天给她剪指甲时,指腹上有几处细小的裂口,像干涸的土地。可就是这双手,能把我最爱的糖醋排骨烧得色香味俱全,能在寒冬深夜给我织出暖和的毛衣,能在每个清晨熬出这样一碗恰到好处的粥。
碗底还剩最后一口粥时,母亲轻声说:"慢点喝,别噎着。"我抬头看见她的眼睛,像两潭安静的湖水,映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。原来最浓的母爱,就藏在这日复一日的琐碎里——是凌晨五点半的厨房灯光,是砂锅里翻滚的小米,是吹凉粥汤时小心翼翼的呼吸。
这碗粥的温度,就是母爱的温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