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的小猫咪
我家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,它叫"咪咪",是去年奶奶从乡下带来的。咪咪有着一身雪白的绒毛,像一团会动的棉花糖。它的眼睛圆溜溜的,像两颗晶莹剔透的黄宝石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咪咪最喜欢玩毛线球了。每次妈妈织毛衣时,它就会蹲在旁边,目不转睛地盯着毛线球转。有一次,妈妈不小心把毛线球掉在地上,咪咪立刻扑过去,用爪子拨来拨去,追着毛线球满屋子跑,逗得我们全家哈哈大笑。
咪咪还是个"小懒虫"。它最喜欢躺在阳台的软垫上晒太阳,常常一睡就是大半天。它睡觉的样子特别可爱,有时四脚朝天地躺着,露出白白的小肚皮;有时蜷缩成一团,像一团雪球。我经常轻手轻脚地跑过去,想摸它的小肚皮,可它总是灵敏地睁开眼睛,冲我"喵呜"叫一声,然后蹦起来跑开了。
有一次我发烧了,躺在床上休息。咪咪竟然轻轻地跳上床,小心翼翼地趴在我的枕头边,用它毛茸茸的脑袋蹭我的脸。它温热的身子挨着我,发出轻柔的呼噜声,让我感觉特别温暖。妈妈说,咪咪是在关心我呢!
这就是我家的小猫咪咪,它不仅是我的好朋友,更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子。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,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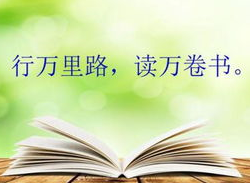
窗台的常客
空调外机上的旧棉垫,不知何时成了灰猫的地盘。它总在午后跳上来,蜷成毛茸茸的一团,尾巴绕着爪子,耳朵随楼下的车鸣声轻轻动。
第一次见它时,瘦得能数清肋骨,怯生生地扒着窗台看我吃面包。我掰了块扔过去,它叼着跑到冬青丛里,回头望我的眼神亮得像碎玻璃。
后来每天清晨,窗台准会多些 “礼物”—— 半片枯叶,或是枚磨圆的石子。有次我感冒请假,它竟蹲在窗台上叫了整上午,声音哑哑的,像怕我不见了。
母亲在棉垫旁放了只瓷碗,盛着温牛奶。现在它总把爪子搭在窗沿上,等我写完作业就跳进来,踩出一串梅花印。阳光斜斜照进来时,能看见它绒毛里的光斑,和我作业本上的字迹一起,慢慢浸暖了整个冬天。
檐下春秋
老屋的屋檐下住着一窝燕子。它们每年清明前后归来,翅膀剪开细雨,在梁上衔泥筑巢,把春天垒成碗状的暖。
起初只是几根草茎黏在木梁上,后来渐渐有了形状。雌燕啄来湿泥,雄燕便飞去衔草,它们配合得如同一个人的两只手。有次大风吹散了未干的巢,我看见它们不眠不休地重建,喙边都磨出了血丝。
雏鸟破壳那天,整条巷子都听得见细碎的啁啾。老燕子捕食的频率骤然增加,从晨曦到日暮,翅膀在屋檐下划出无数道黑线。某日暴雨,它们浑身湿透地贴着巢沿站立,用体温为幼崽撑起一片晴空。
立秋时分,小燕子开始练习飞翔。第一只跃出巢的摔在晒谷场上,扑棱着翅膀像片落叶。老燕子不停在它头顶盘旋鸣叫,直到小家伙终于腾空而起,把歪斜的飞行轨迹写满天空。
霜降前夜,空巢里还留着几片绒羽。母亲说燕子认得回家的路,就像月亮认得自己的窗棂。现在每当我看见瓦蓝的天空,总觉得那倏忽掠过的黑影,是去年屋檐下那封会飞的信。
《窗台上的斑鸠》
春末,一只斑鸠落在我的窗台,嘴里衔着半截枯枝。它警惕地望我一眼,还是决定留下。从此,每天清晨我都能在玻璃外看到它圆滚滚的背影,像一枚温热的石子,在钢筋水泥的罅隙里孵出柔软。
十天后,巢成了:几根枯草、几片碎纸,简单得像孩子的手工。雌鸟卧在里面,羽毛蓬起,像一枚褐色的绒球。我隔着帘缝偷看,怕惊扰这份脆弱的勇气。
六月雨夜,狂风掀翻了半个巢。第二天,只剩一根枝条晃荡。我叹息,却见斑鸠夫妇又双双飞来,嘴里仍衔着希望。三天后,巢复原,巢里多了两枚乳白的蛋。
雏鸟破壳时,我正伏案写字。窗外传来细碎的“咕咕”声,像最小的掌声。我抬头,看见四只黑亮的眼睛同时望向我,带着对世界的第一声问候。
那一刻,我明白:城市再硬,也硬不过一颗想筑巢的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