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平仄叫醒的时光
晨读课的风总带着桂花香。当语文老师用粉笔在黑板写下 “蒹葭苍苍” 时,第一缕阳光正爬上 “溯洄从之” 的笔画,像给古老的文字镀了层金边。
“跟着我读,注意那个‘苍’字要拖长些。” 她的声音忽然放轻,像怕惊飞了诗句里的白露。我们扯着嗓子跟读,平仄在教室里撞来撞去,把玻璃窗震得嗡嗡响。后排的男生把 “宛在水中央” 念成 “宛在水缸中”,引得全班笑倒在课桌上,粉笔灰在笑声里簌簌往下落。
老师没责备我们,反而翻开课本:“你们听,两千多年前的人找心上人,跟现在的我们追跑丢的风筝多像啊。” 她念到 “道阻且长” 时,尾音轻轻上扬,像溯洄路上遇到的浅滩;念到 “宛在水中坻” 时,声音忽然转柔,仿佛真的看见芦苇深处有个模糊的影子。
不知何时,笑声渐渐歇了。阳光漫过课桌椅,把我们的影子钉在课本上。当齐读 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 时,我忽然觉得那些拗口的句子活了过来 —— 原来 “苍苍” 是芦苇荡在风里的样子,“萋萋” 是露水打湿裤脚的潮,而那个 “在水一方” 的伊人,或许是每个人心里,既遥远又明亮的念想。
下课铃响时,桂花香涌进教室。老师合上书说:“诗不是字,是会呼吸的风。” 我望着黑板上渐渐淡去的粉笔字,忽然发现 “溯游从之” 的笔画间,藏着我们刚才没读出来的温柔。
后来每次路过操场边的芦苇丛,总会想起那天的吟诵。那些平仄分明的调子,早把古老的月光,种进了我们正在生长的时光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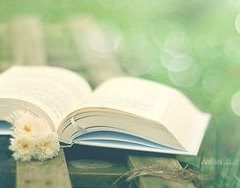
《吟诵声中的觉醒》
那堂语文课前,我从未想过声音可以拥有形状。当老师要求我们齐声吟诵《将进酒》时,教室里顿时响起参差不齐的读书声,像一群离群的麻雀。
"停!"老师突然拍了下讲台,粉笔灰在阳光里簌簌落下。"你们不是在读课文,是在和李白对饮。"他摘下眼镜,喉结上下滚动,"君不见——"这三个字像从胸腔深处涌出的黄河水,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。我们看见他额角的青筋在跳动,仿佛真的看见白发三千丈的愁绪。
轮到我们时,起初依然怯懦。直到后排的体育委员突然站起来,他平时说话总带着篮球场上的粗粝,此刻却把"天生我材必有用"念得像出鞘的剑。我的同桌——那个总是低头绞手指的女生,竟用清泉般的声音接上"千金散尽还复来",尾音微微发颤,像月光下的剑穗。
最神奇的是吟诵到"烹羊宰牛且为乐"时,全班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节奏。我们拍打课桌的声响,化作羯鼓急促的节拍。当最后一句"与尔同销万古愁"脱口而出时,教室突然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阳光斜照在黑板槽的粉笔末上,那些细小的尘埃正在空中跳着千年前的胡旋舞。
下课铃响,我们才发现手心里全是汗。走廊里其他班同学好奇地张望,他们不会知道,刚才这间普通的教室里,四十个现代少年的灵魂,曾通过文字与盛唐的酒仙击掌相和。我的语文书第56页至今留着那天滴落的汗渍,形状像极了小小的酒樽。
《课堂上的吟诵》
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,语文老师抱着一摞泛黄的古籍走进教室,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洒在讲台上,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墨香。
"今天,我们不讲课,来吟诵《诗经》。"老师的话让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。她翻开《关雎》,先是轻声诵读:"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......"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,又像是穿越千年的回响。
我跟着老师的节奏,试着张开嘴,却发现古诗的韵律与现代普通话截然不同。"古人吟诗是要拖长音调的,"老师解释道,"来,跟着我念——'关——关——雎——鸠——'"。教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吟诵声,有的同学声音清亮,有的则略显生涩,但都认真地跟着老师的节奏。
渐渐地,我找到了感觉。当"窈窕淑女"的"女"字被拉得悠长时,仿佛真的看见了一位温婉的女子站在水边;当"君子好逑"的"逑"字轻轻落下时,又好像感受到了古人那种含蓄的情感表达。我们的声音时而高亢,时而低沉,像一条蜿蜒的小溪,在教室里流淌。
最有趣的是吟诵《蒹葭》时。"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......"老师示范着用不同的声调吟诵同一句诗,时而如清泉叮咚,时而如暮鼓晨钟。我们跟着尝试,有的同学把"在水一方"的"方"字拖得老长,惹得大家会心一笑;有的则把"溯洄从之"的"之"字念得特别重,像是在用力划船。
下课铃响起时,我们仍意犹未尽。这堂特别的吟诵课让我明白:古诗不仅是用来背诵的文字,更是可以吟唱的音乐。那些平仄起伏的韵律里,藏着古人的喜怒哀乐,也连接着我们与千年前的文化血脉。现在每当我读到《诗经》,耳边总会响起教室里那此起彼伏的吟诵声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