染缸里的星辰
外婆的染坊藏在巷子深处,青石板路上总晾着蓝印花布,风过时像翻动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海。她总说这些蓝白相间的纹样是有灵性的,得用清晨的井水调靛蓝,再掺上晒干的板蓝根叶,染出的布才会透着月光般的清辉。
我第一次学扎染是在十岁。把白布折成菱形,用棉线密密缠绕时,指尖被勒出红痕。外婆握着我的手示范,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蓝,像藏着几粒蓝宝石。“你看这冰裂纹,” 她展开染好的手帕,蓝底上的白纹蜿蜒伸展,“得让线勒得松紧不一,才像初春河面解冻的样子。”
去年冬天,染坊的老缸裂了道缝。外婆蹲在地上抹水泥,呼出的白气裹着她的银发。我搬来新的陶缸时,发现她正把碎布拼贴成床单,那些边角料在她手里变成飞翔的鸟、游动的鱼。“别小看这些碎布,” 她拍掉手上的灰,“老手艺就像这蓝印花布,得有破有立才能活。”
现在每个周末,我都会去染坊帮忙。阳光透过木窗照在染缸里,靛蓝色的水面晃着细碎的光,像盛着一缸揉碎的星辰。晾在竹竿上的新布随风摆动,把影子投在墙上,忽明忽暗间,仿佛看见无数双手在时光里交替,将这份蓝一直延续下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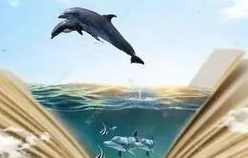
墨香里的传承
祖父的书房里永远飘着墨香。那方洮河砚台摆在窗边,像块凝固的夜色,每次推开雕花木门,都能看见他佝偻着背在宣纸上运笔的身影。
十岁那年,祖父第一次把着我的手写毛笔字。他的掌心粗糙温暖,虎口处有道陈年墨渍,像枚青黑色的痣。"手腕要活。"他说话时,胡须扫过我耳尖,带着淡淡的茶香。我歪歪扭扭写下的"永"字,最后一捺洇成了墨团,祖父却笑着说:"比王羲之五岁时强。"
初中时迷上电子游戏,有次竟把祖父的狼毫笔拿来通游戏卡带。他站在门口,手里端着刚磨好的墨,砚台里的墨汁还在打旋。我以为会挨骂,他却只是把着我的手重新写下那个"永"字。这次我注意到,他中指第一关节处有道弯曲的茧,是六十年执笔磨出的印记。
去年冬天整理祖父遗物时,在砚台底下发现沓泛黄的宣纸。每张都写着同样的"永"字,从稚嫩到苍劲,最后几张的落款是我的名字。原来他悄悄收藏了我这些年所有的习作,连游戏厅包装纸上的涂鸦都没落下。
现在轮到我教妹妹写字了。她的小手在我掌心扭来扭去,墨汁沾满了袖口。当她在纸上戳出第一个墨点时,阳光正斜斜地照在祖父的砚台上,墨香忽然浓了起来,仿佛有只无形的手,正轻轻覆在我的手背上。
做文化传承人
奶奶的针线笸箩里,总躺着半卷枣红丝线。小时候,我最爱蹲在炕边看她纳鞋底,银亮的针在指间穿梭,像条游鱼,"哧啦"一声穿透厚实的碎布层,再用力一拉,线绳便乖乖咬合成结实的针脚。那时我总嫌这活计麻烦:"现在谁还穿手工鞋呀?"奶奶只是笑,手里的针脚却更密了些,像在编织什么看不见的宝贝。
去年春节回老家,发现堂屋的八仙桌蒙了层塑料布,奶奶的针线笸箩被塞进了柜顶。我爬上去打开它,霉味混着熟悉的丝线香涌出来——枣红丝线褪成了暗红,几枚铜顶针锈出了斑驳的花纹,最底下压着半幅未完工的婴儿肚兜,靛蓝底布上绣着并蒂莲,针脚歪歪扭扭,像是被什么急事打断了。
"奶奶,这肚兜给谁绣的呀?"我问。她愣了愣,眼角的皱纹突然软下来:"本来想给你闺女绣的......"我这才惊觉,奶奶的针线活要成"非遗"了。当晚,我搬着小马扎坐在她身边,看她教我认针脚:"纳鞋底要'数纱挑刺',绣花要'先描样后走针'。"她的手背上爬满老年斑,指腹磨出的老茧却依然灵活,带着我重新穿针引线。
现在,我的书桌上摆着奶奶送的绣绷,上面绷着半朵牡丹。周末回家,总看见她戴着花镜,在手机屏幕前研究"国潮刺绣"的教程——原来传承不是守着老物件叹气,而是让旧手艺长出新枝桠。
文化传承从不是宏大的命题。它是奶奶教我认针脚时的温度,是我把刺绣发在社交平台时的点赞,是我们祖孙俩对着手机视频研究新针法的笑声。这些细碎的温暖,才是让文化活下去的力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