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老鼠嫁女》续写
老鼠女儿的花轿刚落进猫洞,红盖头就被爪子勾掉了。新郎咪呜的胡须上还沾着鱼腥味,却对着她作揖:“娘子别怕,我藏了奶酪当喜糖。”
洞角的蛛网挂着串红辣椒,是咪呜特意从厨房偷来的。老鼠女儿摸着花轿上的流苏发呆 —— 当初爹娘说猫是天下最厉害的,可这只灰毛猫连啃鱼骨都要歪着头,睡觉还会打小呼噜。
第三天夜里,咪呜叼来个蓝布包。打开一看,竟是半块蜂蜜蛋糕,奶油上还嵌着颗红樱桃。“张婶家的小孙子过生日,” 他舔着爪子笑,“我蹲在窗台看了三个钟头才偷到。” 老鼠女儿忽然发现,他的前爪缠着布条,是被蛋糕盒的铁皮划破的。
开春时,猫洞成了最热闹的地方。咪呜总把偷来的食物分成两份,干硬的面包渣留给自己,松软的馒头心推给新娘。有次他叼回条小鱼,却先挑出鱼刺才敢递过去,尾巴紧张得直打颤。
鼠王带着卫队来 “探亲” 时,正撞见咪呜在教小老鼠们爬灶台。灰毛猫蹲在地上,用爪子比划着:“这里的瓷砖滑,要像这样弓起身子……” 鼠王举着长矛的手突然软了,他想起当年为女儿选女婿时,说的 “要找最厉害的”,原来厉害的不是尖牙利爪,是藏在呼噜声里的温柔。
如今猫洞的石壁上,挂着串亮晶晶的东西 —— 是咪呜用偷来的糖纸折的星星,每颗星星里都塞着小块饼干。老鼠女儿坐在新郎的尾巴上,看他用爪子在面粉袋上写字,歪歪扭扭的 “囍” 字周围,落满了金黄的粉屑,像撒了把会发光的小米。
厨房的灯光透过砖缝照进来,把两只依偎的影子投在墙上。咪呜的呼噜声混着老鼠女儿的笑声,在寂静的夜里轻轻摇晃,倒比任何唢呐声都更像喜庆的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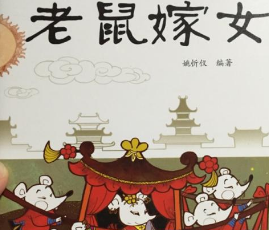
《老鼠嫁女》续写:月光下的婚礼
子夜时分,老鼠姑娘的珍珠盖头被风吹得簌簌作响。她蹲在月饼盒做的花轿里,听见送亲队伍正吱吱呀呀地唱着《月光光》。突然,墙角的破闹钟"铛"地敲响十二下——正是鼠仙婆婆算定的吉时。
"停轿!"鼠爸爸举起绣花针做的仪仗棒。送亲队伍齐刷刷刹住脚步,眼前是堵布满爪痕的老墙。鼠妈妈掀开轿帘,月光正好照在墙缝里:那里趴着只缺耳朵的老猫,脖子上系着用塑料袋裁的领结。
"姑爷别装睡啦!"鼠弟弟把偷来的鱼罐头滚到猫爪前。老猫睁开琥珀色的眼睛,胡须上还沾着下午鼠姑娘偷偷塞给他的奶酪渣。他低头时,项圈上的铃铛叮当作响——那是用瓶盖改的,里面垫着鼠姑娘织的棉花。
鼠爸爸清清嗓子开始念嫁妆单子:"顶级磨牙棒两根,陈年大米三十粒……"突然传来"喵呜"一声,吓得老鼠们集体炸毛。原来是猫姑爷的弟弟来贺喜,嘴里还叼着用蟑螂翅膀粘的喜联。
黎明前,婚礼在冰箱顶上举行。鼠姑娘的盖头是用纱布口罩改的,老猫小心翼翼地用爪子尖掀开。当他们在月光下碰触胡须时,鼠弟弟突然撒了一把偷来的芝麻——落在猫背上像场小小的流星雨。
从此每到半夜,厨房里就响起奇特的二重唱:细碎的啃咬声伴着低沉的呼噜声。而鼠姑娘总把最嫩的鱼肉推到老猫面前,就像当初他假装抓不到她那样。
《老鼠嫁女》续写
老鼠夫妇牵着女儿的手,站在猫宅的大门前。红彤彤的喜烛映照着女儿娇羞的脸庞,可当大门"吱呀"一声打开时,一只吊睛白额的大黑猫正懒洋洋地舔着爪子,金色的瞳孔在烛光下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
"爹爹......"鼠女突然挣脱父母的手,尾巴上的绒毛都炸开了花。老鼠爸爸这才发现,猫嘴角还沾着没擦干净的鼠毛,爪子上黏糊糊的,分明刚吃过宵夜。他后背瞬间窜起一阵寒意,转头对老伴使了个眼色:"咱们改日再来......"
三只老鼠转身就跑,鼠女的小绣鞋都跑掉了一只。他们慌不择路地钻进墙缝,却听见身后传来猫的笑声:"跑什么呀?"那声音甜腻得像裹了蜜糖的毒药,"我连老鼠夹都准备好了呢!"
鼠爸爸一个急刹车,撞翻了路边的油瓶。月光下,他看见女儿正躲在墙角发抖,尾巴尖还在不停地抽搐。老两口突然同时蹲下来,用胡须轻轻碰了碰女儿的脸:"傻孩子,咱们老鼠啊,就该嫁给会打洞的。"
后来,鼠女嫁给了隔壁勤劳的田鼠小伙。新房的粮窖里堆满了金黄的麦粒,他们每天最开心的事,就是比赛谁挖的地道更长。偶尔抬头望见墙头的猫影子,田鼠就会拍拍胸脯说:"别怕,我挖的地道能通到十里外!"
而那只自以为是的猫,至今还在为错过婚宴耿耿于怀。它永远也不会明白,为什么每次靠近那堵墙,地底就会传来"沙沙"的响声——那是老鼠一家在地道里啃玉米的声音,也是他们最动听的笑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