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鞋摊前的暖阳
小区门口的修鞋摊支了有些年头了。张师傅总坐在小马扎上,背后是棵老梧桐树,树皮斑驳的纹路里,藏着他用粉笔写的价目表:换鞋底五元,钉鞋跟三元,缝裂口两元。字写得歪歪扭扭,却像他的人一样,透着股实在劲儿。
每天清晨,张师傅的铁皮工具箱刚在地上放稳,就有人拎着鞋子来排队。他修鞋时总戴着副老花镜,镜腿用细铁丝缠着,左手扶着鞋帮,右手握着锥子,银针在帆布上穿梭的速度快得像条银线。有次我去修运动鞋,看见他正给双破洞的解放鞋缝补,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痕迹。“这鞋都穿成这样了,还修它干啥?” 我忍不住问。张师傅抬头笑了,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菊花:“是楼下王大爷的,他说这鞋陪他种了十年地,扔了可惜。”
张师傅的工具箱里总躺着个铁皮饼干盒,里面装着各种零碎 —— 断成两截的鞋带、磨秃的鞋钉、五颜六色的线团。有回放学,我看见个小姑娘捏着皱巴巴的五角钱来钉鞋跟,钱不够急得快哭了。张师傅摆摆手让她把鞋放下,从饼干盒里找出块粉色橡皮膏,在鞋跟磨破的地方贴了个卡通贴纸:“先对付着穿,等攒够钱了再来修。” 小姑娘破涕为笑,蹦蹦跳跳地走了,他却蹲在原地,悄悄往鞋跟里钉了颗小钉子,又用锤子轻轻敲平。
去年冬天特别冷,张师傅的手冻得裂了好多口子,缠着层层纱布。有天我路过摊前,看见他正给位老奶奶修棉鞋,手指在寒风里抖得厉害,却依旧把每道针脚都缝得笔直。老奶奶要多给他钱,他硬是塞了回去:“说好三元就三元,多一分都不能要。” 老奶奶拗不过他,第二天送来双亲手织的毛线手套,藏蓝色的,指头上还绣着朵小小的梅花。
开春时,修鞋摊旁多了个新木牌,上面是社区主任写的字:“张师傅免费为孤寡老人修鞋”。张师傅依旧每天坐在梧桐树下,工具箱里的饼干盒换了个新的,里面除了针线,还多了包创可贴 —— 他说最近总有些孩子跑来修书包带,怕针扎到手,备着点安心。
夕阳西下时,我常看见张师傅收拾摊子的身影。他把小马扎放进工具箱,将散落的钉子一颗颗捡起来,最后用抹布把地面擦得干干净净。梧桐树的影子在他身后拉得老长,像只温暖的大手,轻轻护着这个小小的修鞋摊。原来平凡的人从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,就像张师傅,用双布满老茧的手,把日子缝补得妥帖又温暖,让每个路过的人,都能感受到生活里藏不住的善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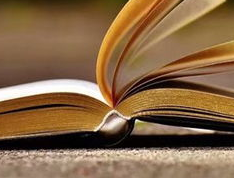
修鞋匠
巷子口的修鞋摊前,总能看到老周佝偻的身影。他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,在那个褪了色的蓝布伞下一坐就是二十年。
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穿过伞面,在老周的工作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他的工具箱已经磨出了包浆,每件工具都有固定的位置:锉刀在左,锤子在右,中间摆着几卷颜色各异的线轴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台老式补鞋机,铸铁的机身被磨得发亮,转轮转动时会发出"吱呀吱呀"的声响,像在哼一首古老的歌谣。
老周修鞋时总要戴上老花镜。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,手上的青筋像盘踞的树根。看他缝合鞋底是种享受——粗粝的手指捏着细针,在皮革间灵活穿梭,每一针都恰到好处。线头在他齿间轻轻一咬就断,那利落的劲儿,完全不像个六旬老人。
常有人劝他用现代胶水,省时又省力。老周总是摇头:"胶水粘的不牢靠,还是针线实在。"这话倒是不假,经他手修的鞋,往往比新买的还耐穿。有次我看见他为一双开了胶的童鞋上线,那专注的神情,仿佛在给自家孙辈做鞋。
雨天是修鞋匠最清闲的时候。老周会捧出搪瓷缸,就着雨声喝茉莉花茶。水汽朦胧中,他的身影与身后的老墙融为一体,像幅被雨水晕染的水墨画。偶尔有老主顾冒雨送来鞋子,他便在伞下点起小煤炉,烘烤受潮的皮革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焦香。
如今这条巷子即将拆迁,老周的修鞋摊也要消失了。最后一次见他时,他正用砂纸打磨一双旧皮鞋,扬起的皮屑在阳光里飞舞,像金色的雪。也许以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用心修鞋的人了,但那些密密匝匝的针脚,会永远缝在记忆的皮革上。
桂花树下的修鞋匠
巷子口的桂花开了,我抱着穿坏的皮鞋走向那个熟悉的小摊。修鞋匠老周头正坐在小板凳上,膝盖上铺着一块蓝布,专注地穿针引线。金黄的桂花偶尔飘落在他斑白的头发上,像撒了一把细碎的阳光。
老周头的手像老树根一样粗糙,指节粗大突出,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色的鞋油。可就是这双手,能让开胶的皮鞋重新挺括,能让断跟的高跟鞋恢复优雅。我常看见他弓着背,鼻梁上架着副花镜,对着光线仔细检查每一道裂痕,那认真的模样像是在修复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
记得去年冬天特别冷,老周头的摊位上却总亮着一盏小灯。有次我的雪地靴开胶了,他接过去时哈着白气说:"这天儿,胶水干得慢。"只见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,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不同颜色的线团,像排队的小士兵。他戴上老花镜,穿针时线头总跟他捣乱,他就耐心地蘸点唾沫,一次又一次尝试。寒风把他的耳朵吹得通红,手指冻得发僵,可那盏小灯始终亮着,像黑暗里的一颗星星。
最让我难忘的是他修鞋时的样子。他总说:"做活要讲究,鞋是人的根,根稳了人才能走得远。"他修鞋不用万能胶,坚持用传统的皮子熬胶;补鞋帮要先垫三层衬布,再缝上细密的麻线。有次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更快的办法,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说:"快工做不出好活计,要对得起人家花钱。"
现在巷子口开了很多新店,可老周头的摊位依然在。那盏昏黄的小灯,那个弯着腰的身影,就像桂花树一样扎根在这里。每次经过,我都会放慢脚步,因为我知道,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,还有人愿意为一双鞋子花费整个下午的时光。老周头用他粗糙的双手,缝补的不仅是鞋子,更是一份渐渐消失的匠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