摆地摊初体验
"走过路过不要错过,精美发夹两元一个!"周六的夜市上,我举着小喇叭,怯生生地喊出了第一声叫卖。这是我第一次和妈妈一起摆地摊卖发饰,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
下午五点,我们就开始忙碌地准备。妈妈从箱子里拿出各种发夹——有镶着水钻的蝴蝶结,有亮晶晶的星星发卡,还有各种颜色的头绳。我负责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摊位上,按照颜色和款式分类排列。夜幕降临时,我们的小摊位在路灯下闪闪发亮,像一颗缀满宝石的小树。
刚开始,我总是躲在妈妈身后,不敢大声叫卖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我的手心直冒汗。这时,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停在了摊位前,她拿起一个粉色蝴蝶结发夹,眼睛亮晶晶的。我鼓起勇气轻声问道:"小妹妹,这个发夹很适合你呢,只要两块钱。"小女孩的妈妈笑着付了钱,我的第一笔生意就这样做成了!拿着赚来的两元钱,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
渐渐地,我越来越放松,开始主动向路过的行人介绍商品。"阿姨,这款珍珠发卡很显气质""同学,这个星空发夹和你的校服很配"。遇到讨价还价的顾客,我也学会了灵活应对:"最低三块钱,已经很便宜啦!"夜市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,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。
收摊时,数着赚来的三十多元钱,我和妈妈相视一笑。这些钱虽然不多,但每一分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和勇气。通过这次摆地摊的经历,我不仅体会到了赚钱的不易,更收获了与人交流的自信。原来,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,就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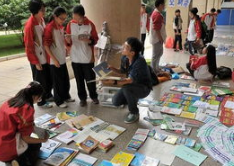
街角的小摊位
暮色刚漫过路灯杆,我和妹妹已经把折叠桌支在了老槐树下。塑料布上摆着她的布娃娃和我的漫画书,风一吹,价签纸像小旗子似的招摇,把 “5 元” 两个字晃得清清楚楚。
第一个顾客是遛狗的阿姨。她的泰迪犬凑过来闻布娃娃的蕾丝裙,妹妹赶紧把娃娃往高处挪:“它会掉毛的!” 阿姨被逗笑了,指着本《童话大王》问:“这本多少钱?我儿子正想要呢。” 收钱时,硬币在铁盒里叮当作响,像在为我们的第一笔生意鼓掌。
中学生模样的哥哥们蹲在摊前翻漫画,指尖划过书脊时特别轻。“这本我有了,” 戴眼镜的男生指着《灌篮高手》,“但你们的卖价比书店便宜两块。”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剧情,买不买倒像次要的,倒把我们的小摊变成了临时聊天室。
妹妹突然拽我的衣角,原来她的兔子布偶不见了。我们慌慌张张地在周围找,卖冰棒的老爷爷突然喊:“是不是这个?刚才掉在我冰柜底下了。” 布偶的耳朵沾着点冰碴,妹妹却把最心爱的贴纸塞给老爷爷:“这个给您,谢谢您。”
收摊时,铁盒里的硬币已经满了大半。妹妹数钱时,发现里面混着颗大白兔奶糖 —— 大概是哪个小朋友偷偷留下的。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折叠桌的边角磕着膝盖,却不觉得疼。
现在每次路过老槐树,我都会想起那个摆摊的傍晚。原来赚钱不只是数硬币的快乐,是陌生人递来的善意,是和妹妹分工合作的默契,是把闲置的宝贝变成别人喜欢的东西。就像那棵老槐树,默默站在街角,却见证着每个平凡日子里,闪闪发光的小温暖。
夜市星辰
黄昏五点半,老周的三轮车碾过夕阳,准时停在了梧桐树下的老位置。他卸货的动作像在拆解俄罗斯方块——折叠桌椅、塑料布、串灯,最后是从泡沫箱里请出的"主角":二十六个玻璃罐,每个都腌着不同年份的春天。
最先吸引顾客的是糖渍桂花。老周用竹签挑出琥珀色的花朵,裹上糯米纸的动作像在包装珠宝。穿汉服的姑娘们围过来时,他特意打开2018年的那罐:"这年的桂花开得最晚,也最香。"路灯突然亮起,照亮他掌心的老茧,那些纵横的纹路里还嵌着去不掉的糖晶。
隔壁卖羊毛袜的大婶是固定搭档。她的毛线针上下翻飞,织补的间隙总来讨杯梅子汤。两人中间的空地渐渐变成共享舞台:写生的美院学生、直播的主播、甚至遛弯的老太太,都会停下来喝口酸甜的时光。老周从不驱赶他们,只是默默把价目牌翻到"今日特供"那面。
收摊前最后一位客人是穿睡衣的男孩。他用游戏币和五颗玻璃球换了罐杨梅汁,老周却额外送了包陈皮糖。"我孙子也爱打游戏,"他边捆绳子边说,"不过那小子现在喝不到我的糖水了。"三轮车吱呀呀远去时,车尾的串灯在风里摇晃,像条被拉长的银河。
现在每次路过那棵梧桐,我总错觉树皮上还沾着糖霜。那些装在小摊上的春夏秋冬,比便利店冰柜里的饮料更多了份人情味——就像老周说的:"腌果子嘛,三分靠手艺,七分靠等。"
摆地摊的一夜星光
周五傍晚,我把家里闲置的课外书、手作发夹和弟弟淘汰的乐高装进纸箱,拉着小车去了市民广场。第一次摆地摊,心里像装了一只扑腾的麻雀。
选位时,我学着旁边大叔的样子,把野餐布铺平,把书按大小排成弧形,又把发夹插在泡沫板上,远远看去像一片彩色的小森林。刚摆好,隔壁卖气球的阿姨提醒我:“小同学,价签要写大,人才能看见。”我立刻用记号笔在硬纸板上写下“通通十元”,还画了个笑脸。
第一位顾客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。她拿起一个星星发夹,怯生生问:“姐姐,能便宜吗?”我脱口而出:“八块!”她付钱时,眼睛里闪着光,那光比广场上刚亮起的灯还要亮。我突然明白,地摊卖的不只是东西,更是快乐。
八点左右,人渐渐多。一位戴眼镜的叔叔蹲在书摊前,拿起一本《昆虫记》,翻了又翻,最后掏出十五元:“不用找零,书值这个价。”我涨红了脸,连声道谢。他把书抱在怀里,像捧着什么宝贝。那一瞬,我体会到“被理解”的温度。
夜风吹皱了广场的灯影,我的纸箱也慢慢空了。收摊时,我把皱巴巴的零钱一张一张捋平,一共赚了九十六元,却在盒底发现一张小纸条——是那个小女孩用拼音写的“谢谢姐姐,发夹真好看”。我把纸条折好,放进钱包夹层。
回家的路上,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赚钱可以这么温柔,讨价还价也可以这么真诚。那一夜,广场的星星很亮,而我心里,也亮起了一盏属于自己的小小灯。
“地摊”见闻记
早上,我和妈妈要去商业街买东西。经过枫南小区门口时,只见路两旁有许多的小贩在摆地摊,有的卖水果,有的卖蔬菜,有的卖玩具的,也有卖生活用品,真是无所不有!
我正想过去看一看有没有我喜欢的玩意儿,忽然只听见一个小贩大叫道:“来了!来了!快跑!”然后迅速地收起放在地上的东西,放在箩子里,往肩上一挑,飞快地朝旁边的弄堂里钻去……这一系列的动作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完成了,简直是训练有素!但是弄得我莫名其妙,奇怪的现象还不至于此,所有的小贩们好像是在谁的指挥下一样,也都迅速的收拾好东西,一时间飞也似的跑得没有了踪影……
我好不奇怪,连问妈妈: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他们跑什么呀?”
妈妈告诉我,这地方是不可以摆地摊卖东西的,这会影响人们行走行车,也会影响市容,管理人员看到了可能要罚他们的钱,或者要没收货物什么的,所以这些小贩们都怕被抓住而纷纷逃走。
我就问:“那他们在什么地方才可心安地买卖呢?”
妈妈告诉我,买菜在菜场,买服装在小商品市场,但是这些地方的摊位是要租赁的,而且要缴税。
怪不得他们要在这些路旁边摆,少付许多钱,占个便宜。
我真是替这些人感到为难:摆在路旁吧,是不允许的,也是不该的;不摆呢,去租个正式的摊位,可能又不够有钱,贩卖的这些自家货,赚不了多少。不过,如果他们不怕辛苦,也可以到乡下去叫卖,不是方便了人又利了自己吗?
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行,不禁陷入了沉思……
